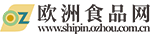渭北是丘陵地势,原先,人们大多住在窑里。
清晨,我听见喜鹊“咔嚓咔嚓——”发出声响,它们在外婆家院外粗壮的洋槐树上叫着。我觉得它们的叫声有铁的质感,像是有人用黑剪子在铰硬铁丝。紧接着,喜鹊“扑棱棱——”飞走了。我想,一定是外爷把牛从牛圈里拉了出去,拴在洋槐树旁的一棵桑树下了。此刻,牛发出的动静把喜鹊惊飞了。
一只灰色的猫悄无声息地赖在我的被窝里,我伸手抚娑了它,它便“呼噜呼噜——”念起经文来。猫诵念出的经文,人是听不懂的。我掀开被子,光着脊背披了棉袄,爬到炕头,手越过炕头的坯墙,抓过一只冷馍来。馍放在酱油色的馍盆里,馍盆是瓷器,在昏暗的窑洞里微微泛着光亮。馍盆放在一个老瓮的青石盖子上。老瓮里装着麦。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立在炕上,上身披棉袄,下身赤精,抱住馍使劲啃了一口。紧接着,我把馍举在半空,模糊不清地叫出“嗷吆——”一声。
院子里的椿树下,一个活物“启动”了,它似乎冲散了在不远处的梨树下吃食的鸡群。公鸡 “咕……”地叫出半声,飞跃到院子里的矮墙上,母鸡们惊慌逃窜,它们的爪子轻轻击打院落里的黄土地,发出细小却不乏清脆的禽类脚步声。
“哐啷——”一声响,半扇门被撞开了,太阳的光柱瞬间照亮了窑洞。微尘舞动在空中。光亮和微尘裹挟着一只大黄狗闯进窑洞里来。黄狗叫作:麒麟。听见我的召唤,麒麟兴奋着摇头摆尾,立起身子,把前爪搭到炕沿上。我彻底醒来了,我在炕上跳了那么几下,俯下身子,掰一口馍,塞到了麒麟的嘴巴里。麒麟吃着馍,我蹲在炕沿上,轻轻地拍打了它的头。
外婆在窑外面的简易灶房里做饭,灶火里燃烧着的似乎是晒干了的玉米茬,“噼里啪啦——”发出爆鸣声。外婆似乎小声嘟囔:“可糟蹋粮食哩!”不久,她对着窑里叫喊:“快饭时了,赶紧起!”
我一边应着声,一边和大黄狗麒麟继续玩耍,直到外婆叫个三五遍,才不情愿地套上棉裤,系上棉袄纽子,翻身下炕,穿上叫做“棉窝窝”的棉鞋。穿戴好后,我站在炕畔,把手伸回被窝里,要把仍闭目的猫揪出来。我的意思是,既然我要起炕了,大家就都不要睡了。
灰猫没有大黄狗那么温顺,我揪它的时候,它窜出被窝,伸长爪子,到我的脸上抓了个血印子。这是要反了天了?我捂着脸要打猫,灰猫呲着牙,梗着脖子,气鼓鼓地顺着支护窑口的木顶柱爬上去,从窑顶部的哨眼里逃跑了……
■ 曾住过的窑
我每天都要打量一番我们的窑洞。
窑的前部,炕占了一大半。炕对面放着一张桌子,桌两旁是两把方椅子。桌旁有一个四方黑柜子,柜子里面放着少许衣物,也放着外婆的针线蒲篮以及一些核桃、红枣之类的干果。
渭北人形容一个人家里有财物,会说那家人的柜子里有“老鼠咬不动”。啥东西是老鼠咬不动的呢?想来大家要描述的应该是金银之类坚硬的事物吧。外婆的黑柜子里不会有金银之物,倒是也有一个“老鼠咬不动”,它是啥呢?我父亲是个煤矿工人,他从煤矿上带回来一块“油石”,是长方体状的一块小小的磨刀石。我外爷多次要用那块小磨石磨镰刀,外婆不让他用,说把镰拿到河里的石头上蹭几下就可以了,一个烂镰么,还值当用那么高级的东西?同时,外婆把方方正正、小巧美观的“油石”放在柜子里,也算是当了个“老鼠咬不动”。
窑的后面,顺着窑墙,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瓮。有装玉米、装麦的老瓮,有装面的面瓮……
父亲回煤矿上班之前,买了些秦冠苹果,装在一个同样摆放在窑侧的棒槌瓮里。他指着棒槌瓮里的苹果,专门叮嘱过我:“一天只准吃一个。”
我母亲在镇上的学校里当老师,她从学校里带回来过一些旧书教材,放在瓮盖子上。有时候,我会翻看那些教材,在书本的图画上看乌鸦是咋样喝到水的。
是的,上学之前,我被父母寄放在外婆家,他们在外面上班,我在外婆家过学前生活。
外婆家是个“独家庄”。何谓“独家庄”?意即离大村子有一定距离,居住人口比较少的乡间聚落。“独”在这里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意思,只用来形容人少、偏远,有孤单的意味。外婆家这个“独家庄”,住了三户人。因“独家庄”在大村子的西边,大村子里的人们称呼这里为:西岸,意思也是西边的意思。三户人中,我外爷和外爷的亲弟弟,也即我的四外爷(家族排名)的家庭,算是其中两户。我大姑也在过去的日子里嫁到了西岸,我大姑父家是三户人家中的另外一户。
三户人家都住着土窑,窑洞背靠着一道山梁,山梁的顶部叫梁上。三户人家的粮食都种在梁上。
■ 外婆一家人老照片
窑前不远处,是陇海铁路铜川运煤专线的支线。每天,蒸汽火车头“吭哧吭哧——”拉着装满煤炭的车厢,沿着火车道,从门前经过。每逢饭时,在院子里吃饭,若遇火车经过,须拿草席盖住饭桌,防止蒸汽火车头喷出的炭渣掉落在饭菜当中。
过了火车道,又是一道低矮的山梁,人们叫它为土梁。土梁上长着速生的洋槐树林,外爷们、亲戚们在洋槐树林边放牛、割草、挖药、拾柴……
土梁下不远出,是我们镇通往铜川市的汽车路,汽车路旁有一眼井,人们在那眼井里担水用。
站在窑前的院子里,抬眼望去,南面是一座形似马鞍的土山,土山上挖着一个防空洞,防空洞口有一个歪歪斜斜的柳树。山叫做南岭洼,关于防空洞前的柳树,有放牛娃传言说,那是棵“消息树”。
放牛娃告诉过我,如果有紧急情报的话,是要做成鸡毛信,送到那棵“消息树”下呢。南岭洼山下有一条河,河水较大,一直朝东流。
左手边几十丈远处,是一座种着果木的山,名字叫做北岭洼。我表哥张伟在镇上上小学,他看了一本关于鹌鹑养殖的书。夏天,他带我在北岭洼设置过捕鸟的机关,妄图捉住一只鹌鹑回家养殖。他说他看到过在北岭洼栖息的一种鸟儿,与他在鹌鹑养殖技术书里看到的鹌鹑一模一样。忙碌了很久,我们没有捉到过鹌鹑,倒是在山上摘了好多林檎,把背心扎在短裤里,把林檎塞在背心里带回家,拿井水淘了,吃着还挺脆。长大以后我看书,我发现在北岭洼栖息的鸟儿根本不是鹌鹑,而是一种大山雀。北岭洼山下也有一条河流,是小小的溪流。日常,我的亲人们在这条小溪流里饮牛、洗衣,等等。
三户人家相互是亲戚,孩子们也都是堂兄弟、表兄弟、表姊妹……在我表哥要上学而其他生活在“独家庄”的孩子都比我小的情况下,我在西岸的孩子们中间,属于首领级人物,也即:“娃娃头”。我们在西岸的童年生活,可能没有大村庄里的孩子们那么多元,但是我们这一伙人干脆就独自拥有了梁上、土梁、南岭洼、北岭洼等一系列山岭,以及拥有了专属于我们自己的河流。
我们与生长在山川河流中的生灵一起生长。
我们闻过院子里梨花的清香,数过门前水渠里的金黄色叶子,伸舌头吃过漫天飞舞的雪花,站在山梁上的彩虹下观看过山洪的爆发……
春天的草木刚发芽,我带着我的表弟们在草间寻觅叫做“棒槌娃”的植物小根茎,用䦆头把它们挖出来,用唇齿咂它的甜气——
刚一入伏,桑葚就红了、黑了,我们一伙人挂在桑树上,一吃就是大半天——
收麦的时候,吃食更多了,地边上长着野生的豌豆,它有豆子的清香气……黄亮亮的杏长在山野间,我的“士兵” 们摘了黄杏给我“上供”——
夏天,外爷给我用钢筋从铁匠铺里打了核桃刀,我偷偷拿出外婆藏在柜子里的“老鼠咬不动”油石,将核桃刀磨得锋利,找个大核桃树剜核桃吃,青核桃汁水把我的手染得乌黑,把胸前的衣服染到洗不干净——
在每一个要玩耍和寻觅吃食的日子里,我骑在外婆家门前一棵大杨树上天然生成的人字形“宝座”上,吩咐我的表弟“士兵”们去捉一只螳螂前来问话。我举着螳螂,看着它的左右大臂,问:“螳螂,螳螂,狼在阿达哩?”螳螂果然就舞动了它的左臂或右臂,它舞动哪边,我就认定哪边有狼。这是毫无依据的占卜术,狼早已在村落周边绝迹,只是说,我每天用螳螂的启示来完成我当“娃娃头”的仪式。接着,我把衣襟拨往身后,手指相反的方向,发出号令:“兄弟们,给我冲!”
■ 小时候的“宝座”
大黄狗麒麟跟着我一起“冲锋陷阵”。
灰猫从杨树叶子里伸出脑袋,警惕地看着我的举动。
牛围着桑树转起了圈子,它颈下的铃铛被我惊吓到响个不停。
深秋,黄叶落满了山间道路。我拿着扫帚和笤帚,去外面扫落叶。外婆用落叶烧炕用。
落叶一经点燃,烟气就从土炕的缝隙里弥漫出来,在窑底地面上形成一层厚厚的烟雾。我端上一缸子凉水泼在窑洞门口,把烟雾往外引,同时拽住黄狗麒麟的耳朵,把它拽到烟气里,看它被烟雾呛着的狼狈。
外婆患了气管炎病,闻见烟气就猛烈地咳嗽。就算烧炕的烟气逐渐消散,到了夜间,外婆还是咳嗽不止。听着外婆持续不断的咳嗽声,我蜷在被窝里,像一只受到惊吓的老鼠。我大舅给外婆买着产自江阴的梨膏糖药,那药物儿似乎很贵,外婆并不舍得按量按时吃。她常常在炕头放着一个梨,实在咳嗽得不行了,才会咬上一小口,含在嘴里。外婆的牙快掉光了,我小心翼翼地听着外婆用牙花咂摸着梨汁,抚摸着在我怀里念诵经文的灰猫,慢慢进入梦乡。
寒假里,上小学五年级的表哥张伟回到家里来,他在镇上听闻了一种土方子,说是如果捉来蝙蝠,在烧热的瓦片上将蝙蝠烘干,磨成细粉吞服,有治愈气管炎病的功效。
表哥寻来了矿灯,背了装有随身物品的挎包,指挥我提了几个空罐头瓶子,我们穿过汽车路,淌过山下的河流,顺着小路上了南岭洼山,向“消息树”爬去。
“消息树”是个大柳树,它哪里是什么“消息树”啊!那不过是放牛娃看过某个电影后,为大柳树起的这么一个有想象力色彩的名字罢了。大柳树背后的防空洞是特殊年代修建的,原本为了防止出现空袭事件而修成,但是没有派上过用场。我表哥张伟在书上阅读了蝙蝠会躲在洞穴里冬眠的句子,他认定我们可以在防空洞里寻觅到这一味“药剂”。
防空洞的入口已然是倒塌了,仅留下一个狭窄的孔洞,只容一个人钻过。表哥头戴矿灯,先钻了进去。进去后,他点燃了背包里携带着的蜡烛——他在课外书上学到了判断缺氧的办法,蜡烛要是熄灭了,说明氧气稀薄,我们就要迅速撤退。点燃蜡烛过了一会儿,我哥命令我也钻进防空洞,他指着燃烧着的蜡烛火苗道:“空气很足!”火苗朝洞内倾斜,我哥判断:“肯定还有别的出口,气流把火苗朝里面吸呢……”
我很崇拜我的表哥张伟,我毫不犹豫地跟在他的身后,我们一步一步走入防空洞深处。
年月过去太久了,防空洞里到处有倒塌的痕迹。能看出来,人们当年修防空洞时,费了很大的力气,硬是在南岭洼这么大的山里挖出了深深的土巷道。洞里面错综复杂,有一些很开阔的去处,可能是人们要用来聚集、开会、议事、居住的地方;洞壁上也有大小不一的洞穴,应该是人们想用以仓储粮食、堆放物品以及上厕所的地方,等等。每到一处路口,我哥都要用随身携带的粉笔在路口画上箭头做标记,防止我们在迷宫一样的防空洞里迷路。
我们在大山的肚子里走了有半里路,发现了把身体倒挂在洞穴里冬眠的蝙蝠。有的蝙蝠单独挂在一处,有的则两三只聚集在一起倒挂着。原先在夏日的夜空中,我见过如魅影般的蝙蝠,我以为蝙蝠是如同夜空一样的黑色,没想到它是褐色的。褐色的皮肤下,还有淡淡的黄色、粉色筋膜,蝙蝠就像一种长着肉翅膀的灰老鼠。
表哥从我手里接过罐头瓶子,用瓶口对准倒挂着的蝙蝠,倒扣了上去,然后向侧边一拉,冬眠着的蝙蝠 “扑棱扑棱——”微微跳动着,掉落瓶中。
机智而勇敢的表哥带着我,巡游在南岭洼山的防空洞中,捉了十多只蝙蝠,要为外婆治疗气管炎病。出来洞外,站在“消息树”下,表哥张伟双手叉腰,眺望着外婆家的土窑洞。我永远记得我哥张伟高大的身姿和目光坚毅的样子,他绝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那是一九八八年冬天的事儿。那一年,表哥张伟十二岁,我六岁。
吃了烘干的蝙蝠粉剂,外婆的病情并无好转。我们琢磨是否是烘干的方法有问题,是不是没有把蝙蝠烘干到能够治病的程度?又或者是不是我们用来烘干蝙蝠的瓦片不符合医病的标准?
外婆咳嗽不止,外婆的哥哥从她娘家捎来了话,让她回家住几天。
外婆带着我去“熬娘家”。听闻了外婆关于偏方的疑惑,外婆的哥哥亲自将蝙蝠粉剂放在他们村里的砖瓦窑上进行了再度烘干。很遗憾,作用还是不明显。
回家之前,外婆哥哥家的母猪产下一窝猪崽,似乎因为没有帮到妹妹治病,外婆的哥哥心怀愧疚,送给我们一只猪崽。
外婆是旧社会生人,是被缠了小脚的,再加上一直咳嗽,她自己无力背负起一只猪崽,便把猪崽装在化肥袋子中,使用一根木棍做杠杆,我和外婆一起把猪崽抬回了家。我们抬一抬,歇一歇,走八里路抬一只小猪,我们婆孙俩走了一个下午。
那只猪崽长得是真好看,干净、漂亮,身上的毛乌黑油亮。我每天在火车道两旁的田野里拾草给猪吃,我拾着被叫做“油勺勺”、“羊脐眼”的野菜,也拾着饱含果实的豌豆科植物……拾草的时候还可以在草丛里发现火车车厢里掉下来的小煤块,也便拾了煤块放在篮子里。回家后,我把小煤块倒在家里的煤堆上,把猪草倒在猪食槽里。看着我们抬回的猪吃着我拾回来的鲜嫩鲜嫩的猪草,我用指头在猪颈上挠了起来。猪很舒服,我很快乐。
■ 外婆家门前的铁道
我姐在春夏之交的一个周末回到外婆家,她也想给猪拾草,还想给家里拾柴。于是,她带着斧子前往土梁干活。
我姐唱着从学校里学来的歌曲,挥舞着斧头,要干一番大事业。不曾想,没挥舞几个回合,我姐一斧头剁上了一个隐藏在地下的“地窝峰”蜂巢。好家伙!一阵黑风从地面刮起,铺天盖地的野蜂朝我姐奔涌而来,把她蛰得连滚带爬,嘴里只管喊“妈呀——”
幸亏我四外爷在土梁上放牛,看见蜂把娃蛰了,摘下头上戴着的草帽,连扑带打把我姐护住,救下她一命。
我姐不知被多少蜂蛰了,头被蛰得肿成了皮球。一段时间里,她上不了学了,专心在家养蜂伤。
这一来,我在表兄弟、姊妹们中的首领级地位被我姐取代了,我的“士兵”们天天都在围着她转。就连我这个“娃娃头”,也成了她的“差使娃”,她睡在炕上指挥着我的行动。
我姐指挥我去我大姑家的小园子里偷苹果。那个季节里,苹果长得还没有乒乓球大,但是架不住她想吃。我偷回一次,她三下五除二就把偷回的果子吃光了。接着,让我继续去偷。
我再次去园子的踪迹被我姑家表姐发现了,她推了我一把,我一脚踏空,从园子旁的土崖上摔下去了。我大姑从土崖下路过,看见她女儿把我推倒了,连忙叫喊已无济于事。但是,我姑看见我被推倒了,却没看见我掉下土崖。我表姐在土崖上,也不知我被推到哪里去了。
原来,土崖当中生着一大丛山楂树,山楂树丛拦住了我。
土崖高丈许,摔下去必定是没命了。我是被山楂树救了一命。
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是,我记得我的悲伤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 我小时候
先是大黄狗麒麟出了事,就在我掉落土崖的第二天。
大黄狗麒麟跟随大人去汽车路旁的水井担水。大人在井轱辘上绞水,麒麟卧在井边不远处,离汽车路尚有一些距离。一辆工具车故意向麒麟驶去,压死了它。
据担水的大人说,我们的爱犬跳起来哀鸣了一声。大人还说,那辆工具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两个男人,看样子他们准备把麒麟抬到车上拉走。大人从井边向狗跑去,两个男人上了车,疯狂驶离。
我们的狗被坏人谋杀!
我哥从学校回家,听闻消息后,一直哭着,吃不下饭。我看着他在家门口竖着的磨盘上画下了我们的大黄狗的画像,一旁写着四个字:爱犬麒麟。他画画儿的时候,把衣袖哭湿了。
夏天的一个夜晚,外婆带着我在门口的大杨树下歇凉,天上的月亮很明亮,星星都在眨眼睛。外婆给我说月亮里有嫦娥,嫦娥怀里抱着一个兔儿。外婆也指着星空给我说天上的河。说完了天上的河,她还说我们脚底下的土地里也生活着小人儿,说是几里几里外谁家里盖房挖地基,一下就挖出来许多小人儿,那些人跟我们的手指头一样大,他们坐的马车大小与洋火匣子差不多大……外婆正说着,我听着入迷,从门前的火车道上走过来一个人,他来自大村庄。来人把我外婆叫着婶婶,说要借我们的猫用一用,说他家里的老鼠泛滥了,需要一个厉害的猫过去把老鼠消灭了。
外婆一边咳嗽着,一边“咪……咪……咪……”呼唤着灰色的大猫,猫乖乖地跑在外婆腿边,蹭着外婆的裤脚。外婆用绳子把灰猫拴住,交给了前来借猫的人,借猫的人说就用个三五天,顶大一个礼拜就给婶婶把猫还回来。
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了,没有见人来还猫,外婆托门前路过的人给借猫的人捎话,看那人把猫用毕了没有。过了两天,借猫的人没有来还猫,也是托人捎了话来,说是他把猫拴在家里养了两天,谁知道绳子松了,猫带着绳子跑了,结果我们的灰猫爬到电杆上,绳子缠住了电线,把猫吊死在电杆上了。
外婆无话。
晚间睡觉,外婆在咳嗽,我躲在空落落的被窝里小声啜泣,我的被窝里再也没有灰猫念诵的经文,我不知道如何安放灵魂。
一九八九年秋季再开学的时候,外婆把我送到大村里的小学去念书。我在学校里呆了不到三天,开始头肿、头疼,外婆道:“好吧……好吧……再逛一阵子吧……”
外爷的身体也不好了,他年轻时患了腰疼病,年老后驼背了,一年比一年严重,放牛、割草、半夜起来给牛拌料都不便利了。经过外爷和外婆的商量,在集会的日子里,外爷拉着家里的牛,把牛在牛羊市场上卖了,卖了五百捌拾元。
冬天,我父亲从煤矿上回来探亲,探亲假在年前用完了,过年期间他需要回去上班。他与母亲商议,要带着我一起去他工作的煤矿上过年,要把我姐留在外婆家。原因是,我还小,坐车可以不用买票,而我姐是需要买票的。
我与父母不常见面,与他们是有陌生感的,我扭着头说:“我不去!”而我姐则偏偏要跟着去。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父母妥协了,他们带我姐去矿上,把我留在外婆家过年。他们出发的那一天是腊月二十三,外爷从外请了杀猪匠来杀猪——我们的猪崽经过一年的养育,已经成了大肥猪了。那是多么好的一只猪啊,人们为什么非得杀它呢?
我父母、姐姐在镇上的火车站坐上了拉煤火车后面挂着的一列绿皮车厢,他们顺着火车道在上午九点半经过我外婆家门口。我骑在门口杨树的“宝座”上,瞅见我父母、姐姐笑着,他们从绿皮车厢里伸出头来,叫着我的名字,向我招手,给我抛出两包瓜子和一把水果糖。这个时候,我听见院子里绑缚猪的地方,我的“猪崽”发出了一声惨叫。我哭了,大哭。
外婆咳嗽着,抚娑着我的脑勺。
院外的桑树下只有几只鸡在拉着鸡屎,我抬头,模糊了的眼睛没有在桑树旁的洋槐树上瞅见一只喜鹊。
作者 | 王文东 | 陕西人




















Copyright 2015-2022 欧洲食品网 版权所有 备案号:沪ICP备2022005074号-23 联系邮箱: 58 55 97 3@qq.com